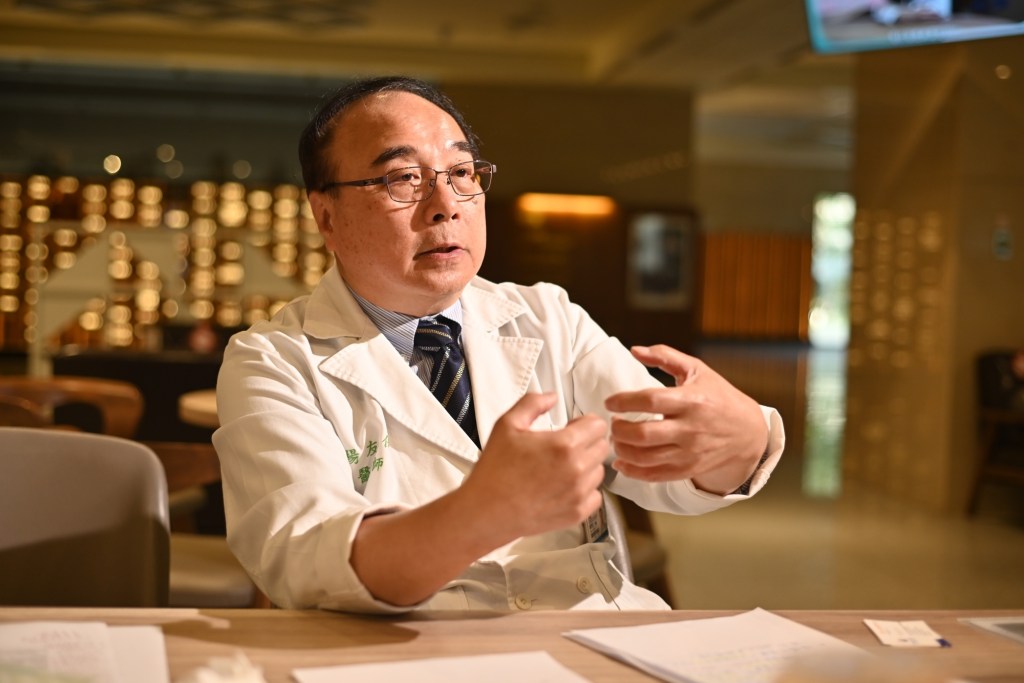(台北內科週報第711期/2025年12月8日-2025年12月14日)
【以書會友】我是1953年6月出生在新竹,家中排行老大,有兩個弟弟、兩個妹妹。我的家庭背景非常特殊,可以說是書香與畫墨並存的藝術之家。祖父陳開泉是上海美事國畫組的藝術家,曾是劉海粟教授的得意門生;父親陳祖儒,是一位書法家,還曾擔任老師。我從小耳濡目染,家中到處是筆墨紙硯、古今詩文。
父親從小就希望我成為一位畫家。他自己雖然寫得一手好書法,但不會畫畫,因此對祖父那一代的藝術志業,總有一份無法實現的遺憾。這樣的期待,便悄悄地落到了我身上。
然而,我並不理解他的心情。我說我想念書,想考醫學院,他非常驚訝,問我:「你要當醫生?為什麼要當醫生呢?」我也說不上來,只是因為我的好朋友,他爸爸是蔡小兒科的,我覺得當醫生看起來也不錯。父親和母親聽了,滿臉疑惑地互看了一眼,像是被這突如其來的決定打了個措手不及。
我從小看到爸爸每天寫字、寫打油詩,那是一種幾乎宗教式的日常儀式感。他從來沒有正式教過我們寫字,反而會罵我字寫得不好,叫我要改進。我也就更加排斥。即使他希望我學畫,還特地到處幫我找美術老師,把我暑假寒假排得滿滿的畫畫課,我心裡還是想:「畫圖有什麼用?我想念書啊!」
那時,我根本無法理解他那份沉默的愛和期望,直到我長大了,才明白他其實只是想傳承某種家族的精神。我的小女兒從小就愛畫畫,畫得很有感覺。當我父親看到她的畫時,彷彿看見了希望,高興地送她一本李可染的畫冊,還特別說:「李可染是你阿公的同班同學,這本畫冊上寫著『繼往開來,承先啟後』,我們家終於有人會畫圖了。」
他是真的開心。那是一種家族精神有了繼承者的釋然。我也漸漸重新拾起畫筆,開始創作,甚至有人將我的作品收錄在《中國收藏》雜誌,還為我做了一本專輯。
我想,如果我爸爸還在世,看到我今天會畫畫了,一定會非常高興。他過去常常會為我寫字,有時候還是打油詩。他說:「寫書法、畫畫,其實是一種人格養成的訓練。」
我過去不懂,現在懂了。那些當時讓我抗拒的事,其實是一種家族精神的延續,只是方式不一樣。我沒有成為畫家,但我選擇了醫學,另一種方式去對生命、對人、對家庭,盡一份責任與傳承。
我有兩個女兒,大女兒在澳洲當家庭科醫師,小女兒則在美國當眼科醫師,兩個也都選擇了醫療這條路。或許我們家沒有繼續做藝術,但從我開始,我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來照顧生命,守護人群。我想,這也是我們家的一種藝術,只是畫布換成了人生。
高醫出身、馬偕扎根
1971年,從新竹中學畢業,第一次考上的是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。但不甘心,覺得應該有更大的空間可以發揮,於是隔年重考,錄取了高雄醫學院的醫學系。一同入學的同學中,有不少日後在醫界嶄露頭角的人,包括侯明鋒(侯友宜的哥哥;前高醫大附設醫院院長),張建國(秀傳醫療體系研發長)、鐘育志(前高雄醫學大學校長)等等。
我念到1979年,足足7年畢業。那是當時的醫學教育常態:前5年是基礎醫學,後2年是臨床與實習。我用功讀書,以第一名畢業,榮獲「杜聰明博士獎」,對我而言,是個莫大的肯定。
畢業後,我服兵役,在臺中中興嶺851醫院擔任軍醫。退伍後,進入臺北馬偕醫院,從1981年起開始接受婦產科的住院醫師訓練。那時的馬偕醫院,是一個非常重視制度與紀律的地方,藍中基教授是主任,帶給我們很多臨床上的榜樣與嚴格要求。我與季明光、葉能貴、林鴻偉等人一起輪班、接生、照顧病人,住院醫師的生活忙碌但充實,許多片段我後來都寫在臉書上,也成為我的生命記憶的一部分。
升任總醫師時,李義男主任對我說:「我們馬偕要學臺大、榮總,發展次專科。」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。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投入產前遺傳診斷,那時這個領域還很冷門,沒什麼人想做。我卻直覺地回應:「我願意。」並且白紙黑字寫下承諾。就是這句承諾,改變了我一生的醫學路。1985年,升任主治醫師,便開始在臺北榮總婦產部學習染色體檢查技術。那是當時全臺灣羊水檢查最多的地方,由耶魯大學遺傳學系的楊蘭平教授回國親自指導。我記得去的時候,他們已經抽了1000多例羊水。
我也去過臺大醫院的羊水實驗室,與謝豐舟教授、柯滄銘教授討論。雖然最後選擇在榮總進修三個月,但這段經驗為我日後創立馬偕的羊水實驗室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1985年,我在馬偕婦產科設立了羊水實驗室。這不只是醫院裡多了一間實驗室,更是為我後來投入鑲嵌型染色體異常與產前遺傳診斷,奠定了里程碑。從那一天起,我知道,我將走上一條不太一樣的醫學之路。

從冷門學科變成國際論文
1990年代初,我在馬偕婦產科持續專注於染色體的研究與實驗。那時,「染色體鑲嵌異常(mosaicism)」仍是一個極為陌生的名詞,幾乎沒有醫師願意投入。當時多數人都選擇發展熱門的基因療法、生殖醫學,而我卻選擇了一條最孤獨、也最不被看好的路。
2011年,我58歲,臨床經驗豐富,也帶過無數產婦和孩子。那一年,我遇到了一個特別的個案——羊水染色體顯示鑲嵌型染色體異常的表現,結果卻是在培養箱培養過程產生的。我不願接受模糊與未知,開始對每一個此類案例進行更深入的交叉檢驗:我採集被培養的羊水細胞,臍帶、臍帶血,新生兒周邊血,口腔黏膜細胞,小便細胞甚至父母雙方的血液,建立一整套「平行樣本交叉分析」的架構。透過染色體培養、基因晶片與分子診斷三重技術,逐漸發現一個關鍵:有些染色體異常只存在於「培養後」的羊水細胞中,卻不見於實際胎兒的體內組織——這代表什麼?這代表我們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檢測標準,可能在極少數情況下,是錯誤的。
這不只是醫學問題,而是道德與倫理的挑戰。如果我們因此建議引產,這孩子可能原本是健康的。如果我們不再深入分析,這些胎兒將在母親子宮中錯失生命的可能。
後來,我更進一步發現,一些產前檢查發現有鑲嵌型的染色體異常的胎兒,其異常染色體的細胞會隨著時間而「消失」,也就是說,在胚胎發育過程中,這些異常細胞會逐步被健康細胞取代,最終出生的孩子完全正常。
我將這些經驗與發現,一一整理為論文,發表於國際醫學期刊。目前為止,已經發表累積至少100個完整案例,所有在產前被診斷為鑲嵌型的染色體異常的胎兒,在出生後大多數都是正常。這些不是數據而已,而是一條條本該消失卻被救回的生命。
這些論文被全球醫學界引用與討論,也讓我意識到,自己這條冷門之路,終於走出了聲音。我不會說這是成功,我只說,這是堅持——在最黑暗的角落,也要有人點起燈,告訴世界:「這裡不能輕忽。」
不只研究,更要救命
我永遠忘不了那些坐在我面前、滿臉淚水的爸爸媽媽。他們懷著期待來產檢,卻收到一紙檢驗報告,顯示「染色體異常」,還特別寫上「鑲嵌型染色體異常」,那是一串讓人困惑卻又驚恐的名詞。他們常常說:「醫生,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孩子好不好。」
但偏偏這就是最難回答的問題。因為這類異常,在當時的醫學標準裡,其實是最模糊的一類。檢驗報告上顯示有30%、40%的異常細胞,可那究竟會不會影響寶寶?誰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證。
我曾經遇過一位李姓夫婦,他們的寶寶在羊水檢查中,發現染色體第10號長臂末端有缺失,異常細胞比例達到35–40%。當時他們已經很沮喪了,但我心中有一絲希望,因為我知道這種鑲嵌型異常,有可能是「胎兒自救」的過程。
我建議他們四週後再驗一次,結果異常比例降到11%。我告訴他們:「這個寶寶正在努力長大,自己修補、調整,你們要不要再等一下?」這句話看似簡單,卻成為這對夫妻願意堅持下去的信念。
後來這個孩子健康出生,我們持續追蹤他數年,所有的發展都非常正常。我不敢說這是奇蹟,但我知道,這是我們用更謹慎的判讀與更完整的資訊,守住的生命。
在那個年代,標準流程是建議再次抽羊水做檢查,但即使重抽,很多時候還是會出現鑲嵌型的結果。大多數醫師會勸引產,因為沒人願意冒風險。但我越來越不安,因為我看過被引產下來的胎兒,外觀看起來完全正常。我開始自問:「我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?是不是用錯了標準?」
因此我開始做一件過去幾乎沒有人會做的事:在這些被引產的個案中,仔細檢驗胎盤、胎兒皮膚、器官與血液樣本,並與培養羊水細胞結果進行交叉比對。我發現,那些染色體異常,有些根本不存在於真正的胎兒組織中。
這種落差,說明了我們可能一直依賴錯誤的依據來做重大決定。我不禁震驚,也更加堅定要改變這一切。從那之後,我不再只做「培養後細胞」的檢查,而是同步採樣未經培養的細胞,使用基因晶片與FISH技術進行判讀。
這樣的流程雖複雜、耗時,但我堅信:如果能多給一對父母一點希望,那就是值得的。我曾經說過:「資訊完備了,決定就在爸媽心裡,而不是檢驗報告上。」這樣的觀念,在當時並不普遍,甚至常被質疑。但我依然選擇堅持,因為我
知道,醫學不是只靠儀器數據,而是要回到對生命的尊重與陪伴。每當看到那些曾經落淚的父母,後來帶著健康的孩子來看我,我心裡只有一個想法:「我們真的一起走過那段最難的路。」

改寫全球醫師新的參考「標準」
過去,產前遺傳診斷的黃金標準是羊膜穿刺──抽取羊水後,將細胞送去實驗室培養,再做染色體核型分析。這項技術確實幫助了無數家庭了解胎兒是否健康,但我卻發現,當結果顯示「鑲嵌型染色體異常」時,醫師與家庭往往陷入兩難。鑲嵌型染色體異常是一種細胞層級的矛盾:有的細胞染色體正常,有的卻異常。當時沒有標準流程能判斷這種混合比例到底對胎兒有沒有影響,多數醫師為了安全,只能建議保守處理,也就是引產。但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:「如果這些異常,是在實驗室培養過程中才出現的呢?」
我開始推動一項新策略:同步分析「未培養」的羊水細胞。我引入了基因晶片(CMA)、螢光原位雜交探針(FISH),以及其他分子診斷技術,直接檢測原始樣本。結果令人震驚:有些在培養後顯示高比例異常的樣本,在未培養的狀態下,其實是正常的,甚至只有極少數細胞出現異常。這代表我們原來所信任的檢測程序,在極少數情況下會產生偽象(artifact),可能導致本來健康的胎兒被錯誤地引產。
這樣的發現,在醫界並不容易被接受。因為這不只挑戰了一項技術,更是對整個產前遺傳診斷體系的質疑。但我有責任說出真相。
我將這些個案系統整理,寫成臨床報告,一篇篇發表在國際醫學期刊中。目前為止,我已經發表100例以上完整研究,每一個孩子在產前都被診斷為染色體鑲嵌異常,但絕大多數健康出生。我把這些結果分享出去,是希望全球的醫師與家長都能知道,有時候,「異常」未必就是結論,而是一道需要更深入理解的訊號。
這些研究,漸漸受到全球同行關注。越來越多國外的醫師,開始使用我所提出的方法。他們不只引用我的論文,更在臨床上實際應用,挽回了無數新生命。
有時我想:如果我當年沒有質疑標準,沒有堅持另闢蹊徑,那些原本可以健康出生的孩子,也許早已被當作統計數字,被埋沒在實驗數據的盲點中。
我相信,真正的醫學不是墨守成規,而是勇於修正標準、改寫標準,讓它更接近真實。因為那背後,不是一行數字,而是一條條寶貴的生命。
拓展了胎盤與基因的理解
當我們談論染色體異常時,許多人直覺想到的是胎兒本身,但我的研究讓我發現,真正關鍵的,往往是胎盤。
我曾經形容胎盤就像是一場馬拉松──當染色體在受精卵階段就發生異常,那條錯誤的線索會一路跟隨著胚胎發展,而胎盤細胞的增殖速度與穩定性,就像跑者在賽道上的節奏:有的衝刺,有的落後,有的乾脆中途退出。
我觀察到,某些染色體異常的表現,不一定出現在胎兒體內,但是會出現於胎盤。這個現象給了我新的啟發──胎盤不只是營養與廢物交換的中介,它本身就是基因組印記(genomic imprinting)之單親二體症(uniparental disomy disordes)之產前診斷的前銷站。
多年來追蹤這些特殊個案其中最讓我關注的就是染色體15「小胖威利症候群(Prader-Willi Syndrome, PWS)」。尤其是母系單親二體症。這些錯誤可能胎盤早期就看出端倪。胎盤表現染色體15由NIPT母血檢測先看到, NIPT是非侵襲性的產前母血檢測。
我提出一個觀點:我們不應該忽略胎盤的角色,反而應該讓胎盤成為產前診斷的前哨。因為很多染色體鑲嵌異常,在胎盤可以先看到也藉由NIPT的科技可先偵測到這些成果也陸續發表於國際期刊,逐漸讓全球的產前遺傳診斷專家注意到:真正的異常,未必都在胎兒看得到;真正的答案,可能藏在胎盤裡頭由NIPT先看到。

用生命守護生命,是我選擇的十字架
很多人問我:「你這樣做值得嗎?這麼辛苦,常常吃不下、睡不好,還要跟體制拔河、跟時間賽跑。」我總是微笑地說:「值得,因為那是生命。」
在馬偕工作的這些年,我看過無數次的落淚,也經歷過一次次的自我懷疑和深夜反思。但我從沒忘記過,醫院的院徽是一個十字架,那不只是宗教符號,更是一種召喚、一種信念:「焚而不燬。」
當年我曾累倒住院,2017年心臟冠狀動脈血管裝支架開刀,術後沒多久我又回到工作崗位,繼續完成我的實驗和追蹤工作。因為我知道,這不只是我的研究,而是病人全家的希望。我不只是做一個醫師,我是在與每一對父母,並肩走過絕望與希望的那段路。
我一直相信,資訊給得越完整,決策就能越有尊嚴。哪怕只是多給一天的觀察時間,或是換一種說法的角度,都可能改變一個孩子的命運。我不是在拯救世界,我只是盡我所能,守住每一個還有希望的生命。
我曾經抱過那些原本「被建議不要留下」的孩子,他們已經長大,有些上國中,有些變成哥哥姊姊。他們的媽媽總是含著淚說:「謝謝你那時候沒有放棄我們。」我會笑著回:「是你們勇敢,我只是告訴你們,還有另一種可能。」
這些年,我把個案整理成論文,發表於國際,也擔任學術期刊主編,就是希望把這些方法和精神傳出去,讓更多醫師知道,有時候,我們可以做得更多。
有人說:「醫學是理性科學。」但我認為,醫學也是情感科學,是人與人之間的陪伴與信任。我選擇的不是最輕鬆的路,但它讓我不虛此行。
我人生最大的成就,從來不是某篇論文或某場演講,而是每一次陪伴父母走過不安、最終迎來健康新生的那一刻。那不只是成就感,而是一種敬畏,一種感恩,一種我願意終其一生背負的十字架。
我始終相信,「用生命守護生命」不只是口號,而是一場長年累月的實踐,是我對醫學、對家庭、對社會所做的承諾。
台灣醫師的兩岸藝術文創之路
我來自藝術世家,祖父是國畫家,父親是書法家。雖然我少年時選擇了醫學這條路,甚至把人生都奉獻給產前遺傳診斷,但藝術從未真正離開過我。只是到了人生下半場,我才更有人生閱歷,也更有生命感觸,重新拾起畫筆,重構我與畫之間的關係。不過,我畫的不只是作品,更是一場希望進入中國及世界的藝術收藏市場。
我曾為《中國收藏》《中國藝術》《藝術市場》《文化月刊》《典藏今藝術》撰稿。雜誌邀請為「台灣精英特輯」撰稿與收錄作品,典藏雜誌還特別出了別冊,這絕不是偶然。這背後,是我10年來對「藝術文創」的熱愛投入。我知道,若想要在大陸市場被看見,你不能只在台灣單一發展,更要讓更多讀者看到我的作品,藉著媒體網路視頻展覽展現我的藝術文創心路歷程,分享我的藝術創作理念。你得進入他們的體系。
我熱愛創作。但我也知道,在這個資訊爆炸與注意力稀缺的時代,單純地「畫得好」是不夠的。你還要讓這幅畫「被看見」、被收藏、被討論、被轉傳。但我認為,這是對作品的負責,也是讓藝術得以傳承的現代方式。藝術家不能再是與世隔絕的苦行僧,而是要懂得站在舞台中心,說出自己的理念與風格與世人分享。
如果我父親還在,他看到我如今的創作,應該會滿意。我終於用自己的方式,把祖父與父親留下的那一筆「文化帳」,慢慢清償。只不過我選擇的方法,是畫筆加演算法,是墨香配戰略,是「兩岸都看見」的藝術佈局。我相信,真正的藝術,是可以溝通的,是可以對話的,是可以跨越海峽的。而這段旅程,也成為我人生中另一種形式的守護與實踐。
(本文摘錄自《婦產科醫師生命之光(下)》1書的《陳持平醫師:從醫學到藝術雙軌人生》,經作者宋永魁教授授權全文刊出)
附:陳持平醫師事略
1953年:出生於新竹,出身書畫世家,祖父為國畫家陳開泉,父親為書法家陳祖儒,自幼耳濡目染人文藝術。
1972年:重考錄取高雄醫學院醫學系,7年後以第1名畢業,榮獲「杜聰明博士獎」。
1981年:進入臺北馬偕醫院,接受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。
1985年:赴臺北榮總婦產部學習染色體技術,回馬偕設立羊水實驗室,為台灣早期產前遺傳診斷奠基。
1990年代:投入「染色體鑲嵌異常」研究,揭示羊水培養檢查的侷限,首創未培養細胞與分子診斷交叉驗證。
2000年起:主編《Taiwa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》,推動台灣婦產科學術國際化。
2004–2019年:歷任馬偕醫學研究部主任、副院長,於陽明、中國醫、國防醫學院等校任教遺傳醫學。
2011年後:提出拯救胎兒計畫,發表多篇國際論文,成為全球臨床參考標準。
2019年:榮獲第29屆醫療奉獻獎,表彰其在守護胎兒生命與遺傳研究上的重大貢獻。
2022–2025年:入選史丹福大學「全球前2%頂尖科學家」,成為國際遺傳醫學界重要學者。
近年:重拾畫筆,以戰略思維跨足藝術經營,積極佈局兩岸文化市場,延續家族精神。